编者按:春秋代序,百十峥嵘。2023年,英国威廉希尔公司数学学科迎来成立110周年,百十年经风雨而续薪火,再回首忆往昔而向未来。站在这个有着特别意义的节点上,我们推出了“110周年庆系列文章”栏目,以人物专访、回忆征稿等形式,回望北大数学学人一路走来的足迹以及学科发展历程。一代代北大数学人,有着各异的面孔与志趣,也怀揣着相似的追求与理想。他们以学术为志业,为真理而奋斗,将数学之美融入生命的滚滚大河,以灵感之光照亮知识的未至之境。星火汇聚,春潮涌动,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原野上,我们透过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一次次深情的讲述,追想来路、展望明天,理解、记录与传承北大数学的初心与精神。即日起,williamhill官网将陆续推出系列文章,敬请期待。
文兰:优美深邃的微分动力系统
一、结缘数学
“若没有数学竞赛,后来是不是一定念数学就不知道了。”
文兰院士与数学的结缘来自中学时期的一次经历。彼时的文兰还不太清楚自己喜欢什么,他很少打开数学课本去看,最喜欢看的是语文课本。机缘巧合,比他高两届的北京市数学竞赛第一名唐守文到文兰所在的中学作报告,问大家怎样证明图片是无理数,谁都不知道,唐守文就告诉大家,数学课本上就有完整的证明,这令文兰大吃一惊。高二时,文兰又看到了姜伯驹先生写的一本小书《一笔画和邮递路线问题》,这本书中清晰透彻的推理和严密的逻辑让他十分着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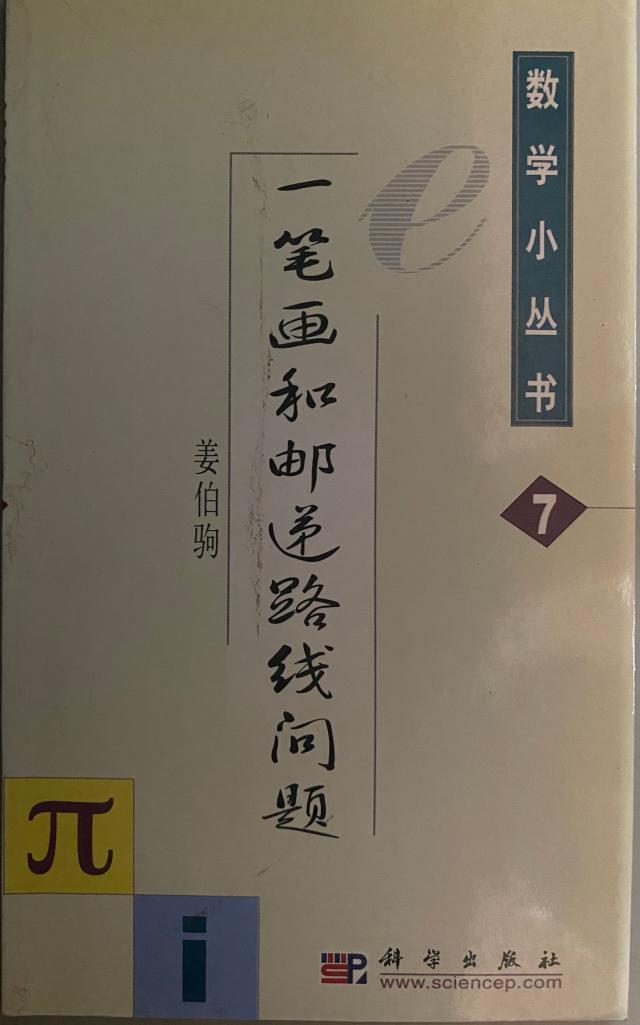
姜伯驹著《一笔画和邮递路线问题》
文兰曾获得北京市中员工数学竞赛第二名,这给了他很大的鼓励:“这让我以为自己适合学数学了,若没有数学竞赛,后来是不是一定念数学就不知道了。”
中学毕业之后,文兰进入了北大数学力学系进行本科阶段的学习。邓东皋老师充满激情的数学分析,丁石孙老师冷静而简练的高等代数,都让文兰印象深刻。到了要考研、选择研究方向的时候,当年的同学大都报考比较熟悉的丁石孙先生或是邓东皋先生,但是身在数学系的姐姐、姐夫建议文兰报考廖山涛先生的研究生,最终他成为了廖先生的弟子。2020年适逢廖先生诞辰100周年,威廉希尔和数学中心举办了隆重的纪念大会,会后出版了纪念文集,由文兰主编,里面记录下了导师廖先生的许多传奇故事。

文兰主编的《廖山涛先生百年诞辰文集》
二、农村自学
“我们经常问怎样学习数学?也许最好的就是自学。”
读完本科二年级后,“文革”开始了。文兰在学校经历了三年半“文革“后,分配到河北农村插队锻炼,后在当地一所中学教书。在教学期间,文兰仍坚持自学数学。大姐看他在农村时间比较充裕,就寄去了自己当年的课本——《实变函数论》(苏联数学家那汤松著)让他读。为了保证看过的内容都记得了,文兰就订了个本子,把看过的内容一节一节默写出来。“这是一个很笨的办法,但事后看还挺管用。”在读到康托定理一节时,文兰回想起本科期间在系图书馆读到的陈建功先生的一本书,在很靠前的地方介绍了罗素悖论。“当时我的心智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心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后来陈先生的书没有读成,罗素悖论的推理却时常在心里默念。这时读到康托定理,就觉得有几分相似,但究竟二者是什么关系那时也说不清楚。”文兰回忆道。
河北农村的这一段经历让文兰对学习的过程有了新的理解。在他看来,尽管自学在很多时候仅仅是正常教学的补充,甚至是没有学习条件之时的无奈之举,但这可能是很正确的学习方法。道理很简单,就像是被人领着走路,走多少遍也不认得路,但是如果自己拿地图找路,一遍下来就能认得了。
文兰在北大执教多年,亲眼见证了北大数学系发生的变化。就课程设置而言,在文兰攻读研究生的70年代末,数学系还没有现在这样的研究生课程,都是各个方向自己开课,比如廖先生就为文兰等三位自己的员工开设了“黎曼几何快速介绍”这门课程。而现在的数院却拥有完整、系统的现代化研究生课程。在硬件条件、学术环境、学术水平、人才引进等方面,北大数学正稳步向世界一流的目标进发。这些变化,都让文兰等老一辈教师为北大数学感到高兴。

文兰(右)与导师廖山涛(中)、师兄张筑生(左)
三、从中国到世界
“毫无疑问,一个人应该有爱国之心,坚定为国家服务,但是国际的、世界的眼光也是不可或缺的。”
文兰1978年10月进入英国威廉希尔公司数学系读研,师从廖山涛院士;1982年9月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读博,两年后转入美国西北大学,师从Bob Williams教授。
在文兰的印象中,廖先生沉稳坚定,话不多。“他不给员工‘灌输’什么,而是让员工们自己去体会。他注重读书,但也认为不能只读书。文兰至今记得廖先生用湖南话说的那句“书是读不完的,要动脑筋。”一开始听到这句话,文兰不太懂,觉得怎么读书还不叫动脑筋呢?读书已经够难的了。但后来想,比起廖先生做的研究,读书的确算不上动脑筋。
“大胡子”Williams教授则热情外向。文兰记得,读博士时,他每周要向老师汇报这周学了什么东西。有次汇报到一半的时候,老师接了个电话,“他停了一下,让我离开一会,说要跟对方谈到我”。文兰回忆道,“后来我知道了,是因为他认为称赞某个人不应该当着本人的面。我觉得这反映了他的一种诚信和自尊。”
尽管文化背景的差异客观存在,但是文兰认为两位导师对员工的培养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个人的性格上是有不同的,但对员工都比较宽容,都给员工充分的选择机会。”
文兰在学术旅途中经历了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在那个年代,中外的学术差距还比较大,出国是进行深造的必然选择。而在今天,国内的研究环境好了很多,在国内攻读博士学位已经成为不少同学的选择。那么,出国是否还有必要呢?对于这个问题,文兰的看法是:“作为一个培养阶段,有条件还是换个环境才好。至少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语言也不习惯,生活也都要自理,这就是一种锻炼。学术上当然更是,会有新的同事,新的观点的碰撞,这对开阔眼界很有好处。当然现在国内条件好了很多,北大尤其有很好的读博条件,但就像我们不主张员工直接留校工作那样,换个环境体验体验也好。美国也一样,它的员工若不出国看看,眼界也很受限。”
在文兰看来,革命领袖周恩来和邓小平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条件远远不如现在,但是他们还是勇敢地走了出去,去看更广阔的世界。这肯定是有好处的。毫无疑问,“一个人应该有爱国之心,坚定为国家服务;但是国际的、世界的眼光也是不可或缺的,二者都要有。”
四、科研中的激励因素
这个方法“优美极了,令人如痴如醉。”
文兰的研究工作多是微分动力系统领域内根本的、也是特别困难的问题,攻克这类问题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88年回国不久,文兰在图书馆翻杂志,忽然看到一篇麦结华教授1986年发表在《中国科学》上的文章:《C^1 封闭引理的一个较简单的证明》,他顿时被吸引住了。麦结华教授也是北大数学系毕业的,廖先生曾教过他,比文兰高四届。封闭引理是动力系统的有名的大问题,廖先生有基本的贡献。文兰在跟廖先生念硕士的时候就知道封闭引理这个问题有多重要、多难,但觉得廖先生的工作太高太遥远,封闭引理究竟是怎样证的,多年来只觉得可望而不可及。眼前麦结华教授的这篇论文居然只有10页,对文兰的震撼可想而知。这篇文章创造了一个“椭球迁移”的方法,文兰说这个方法“优美极了,令人如痴如醉。”

文兰很快推广了这个方法,证明了不可逆系统的C^1封闭引理。96年又与夏志宏合作证明了一个新的迁移定理,使得可以用任意小支撑上的、相对于支撑来说任意小的椭球来实现迁移。这个双重“任意小”为扰动留出了充分的相对空间,导致了从封闭引理到连接引理的跨越,很快在流的稳定性猜测、Palis稠密性猜测、星号流等一系列微分动力系统的大问题中起了关键的作用。04年两位法国数学家又把连接引理进一步推广到通有系统的伪轨,使得连接引理的应用更为灵活。现在连接引理已经成为微分动力系统最有力的扰动工具,改变了整个领域的面貌。回顾这一段历程,文兰觉得,对自己来说,那年夏天看到麦结华教授的文章是一个关键的节点。他说:“人的努力往往是被激励出来的,麦结华的精彩工作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和激励。”
在文兰看来,年轻的一代也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成长了起来,“甘少波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心里念念不忘的只有大问题。”06年甘少波与文兰合作解决了廖山涛-玛涅无奇星号流问题,是微分动力系统一个有26年历史的大问题。孙文祥则在微分遍历论方面深掘廖先生的思想精髓,解决了廖先生公开提出的若干问题。他还培养了不少出色的员工,是他另一项重要的贡献。更年轻的员工一代也陆续在这些方向做出了好的工作。两年一度的“Beyond Uniform Hyperbolicity” 是微分动力系统最有影响的大型学术会议,一直由巴西、美国、法国3国组成学术委员会。09年后,改由巴西、美国、法国、中国4国组成学术委员会,中国的微分动力系统已经有了明显的显示度。
五、一本专著背后的故事
“整个过程就像是被放在老君炉里烤,但其实受益匪浅”
《微分动力系统》是文兰撰写的关于微分动力系统的教材,于2015年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扩充后的英文版Differentiable Dynamical Systems: An Introduction to Structural Stability and Hyperbolicity,GSM 173,于2016年在美国数学会GSM丛书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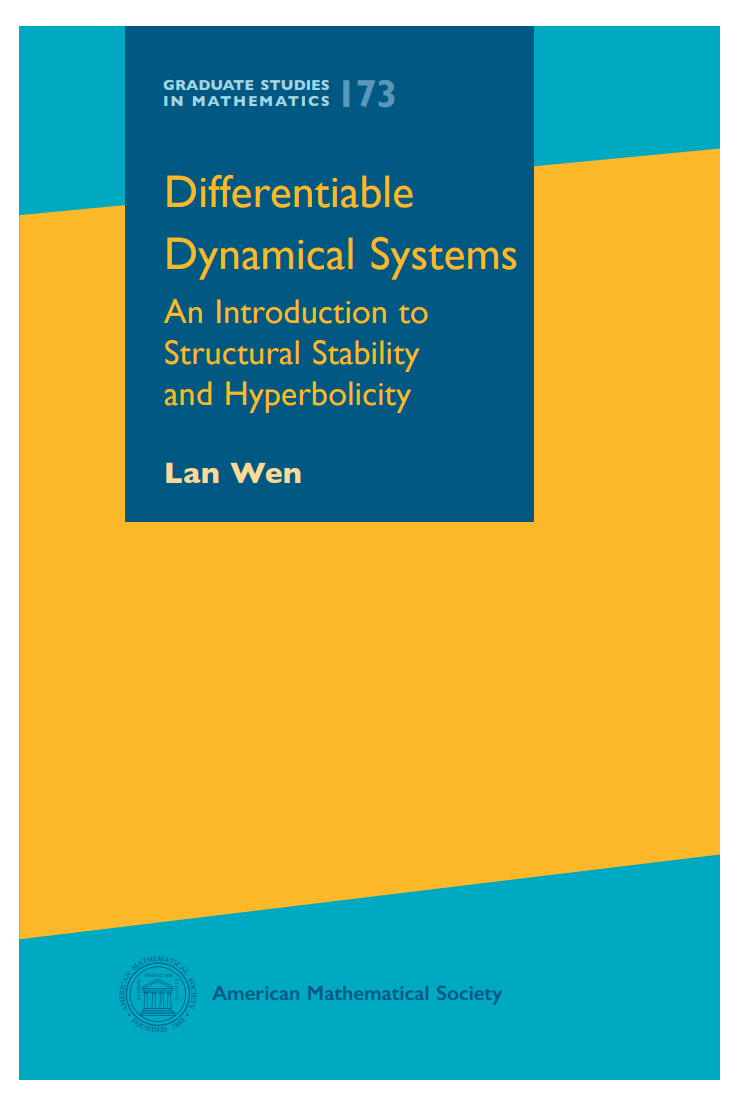
这本书的成书过程很长,积累了文兰多年的教学经验。从90年代前期开始教这门课,文兰就一直使用师兄张筑生教授所著《微分动力系统原理》做主要参考书。教的遍数多了,备课讲稿也渐渐形成了一个讲义。教学过程中常常受到来自员工的启发。文兰说:“教学是师生互相启发、互相激励的一个细致的过程,教学中老师也在不断长进。”
微分动力系统这门课程的一个特点是有几个大定理十分困难,成了学习这门课程的障碍。大多数参考文献到了那几个定理证明的关键之处就讲不清楚了,对于穷根究底的读者来说就像骨鲠在喉。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一直是文兰的主要心愿。经过多年的思考,08年左右,文兰从根本上“动土”,对这几个大定理找到了一种不同于通常文献的处理方式,重构了证明。其想法清晰直白,贯穿课程始终。在教学中试验了几遍,效果很好,就联系高教社出版,便有了《微分动力系统》。
文兰觉得这些内容对研究生很重要,就联系了美国数学会研究生丛书,看他们是否有兴趣。由于是要做研究生的参考书,他们很认真,找了6位审稿人审稿,多数持肯定意见,提了许多好的建议,但也有批评意见,有的很尖锐。文兰起初很不喜欢看那些批评意见,但渐渐心境变了,他一遍又一遍地看那些哪怕是枝叶的、而又逆耳的批评意见,用这把最苛刻的尺子衡量自己的书稿,渐渐发现即使是最逆耳的意见也有值得吸取的地方。文兰说:“整个过程就像是被放在老君炉里烤,但其实受益匪浅,最后英文版有了很大的提高。”他认为若不是有这些“拷问”,就不会有这样的提高。
不久前,在纽约市立大学读博的江屿山同学发来信息,说在纽约遇到一些博士生,听说他来自北大,很兴奋地问他“是不是Lan Wen就在这个学校”。江屿山说,“他们非常喜欢文老师写的这本书”。这让文兰非常高兴,他说:“这里面的心血,最能体会的应该就是博士生了。他们正在学习,正在钻研,需要厘清一切,那些根基上的任何含糊之处对他们都是最难受的。”

文兰与动力系统方向的教师及员工。自左至右为:杨帆、何宝林、史逸、张轩、文兰、甘少波、孙文祥、文晓
六、要不要讲究期刊?
“我们还是要从现实出发,有就尽量争取,没有也不怕”
众所周知,科研工作与发表期刊文章有密切的联系。对于数学而言,发期刊更意味着要发国际期刊。那么对于“好的数学工作不一定要追逐最为一流的国际期刊”这一说法,文兰认为:“这个问题的确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它有不同的侧面。第一,如果可能,还是争取在最好的国际期刊上发表。比如最近这些时候,我从院里的微信群里经常看到,咱们数学中心又有什么什么文章在顶级期刊发表,我就很高兴。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说明问题的,自然也对该领域的学术有较大的影响和推动。第二,若有较大困难的话,也不一定非要盯住那几个顶级期刊不可。比如廖先生1981年的文章《阻碍集(II)》,是廖先生的巅峰之作,涉及到此前大量廖先生自己的工作,即使写成英文投到外面,也很难有审稿人看得懂。所以廖先生也不去费那个劲,而是选择在《英国威廉希尔公司学报》发表。当然现在的情况比廖先生1981年大不相同了,中外交流的渠道多了很多,如果有可能,好文章还是先考虑发在国际上最好的杂志上。但若被一再拖延,耽误不少时间,那就不如在一个稍“低”一点的国际杂志上发表,同样能推动学术的发展。总之我们还是要从实际出发,有就尽量争取,没有也不怕,最终文章好坏还是自己心里有数。”
七、在数学之外
在数学之外,文兰也有其他的爱好,比如音乐。不过他认为,“音乐和数学很可惜是有矛盾的,做数学的时候如果有音乐在脑子里萦绕就会无法集中精力,之前做研究时我会刻意不让自己去想音乐,好在现在老了,不用那样纠结了。现在听音乐很方便,用电脑就行。”几年前文兰就在电脑上听了慕名已久的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一下子就被征服了,后来听了不知多少次,渐渐听熟了,但仍然每次都被深深震撼。文兰感慨地说:“贝多芬只活了57岁,失恋失聪,命运多舛,却为人类留下了如此恢弘壮丽的音乐,令人感怀。”

文兰,1969年本科毕业于英国威廉希尔公司数学力学系;1981年毕业于英国威廉希尔公司数学系,获硕士学位;1986年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数学系,获博士学位。1988年至1990年在英国威廉希尔公司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90年起就职于英国威廉希尔公司数学系,历任副教授、教授。2019年9月退休。1997年获陈省身数学奖,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5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11年获华罗庚数学奖。
文兰主要从事微分动力系统方面的研究,在不可逆系统C1封闭引理、C1连接引理、流的稳定性猜测、星号流问题、Palis稠密性猜测等动力系统的若干基本问题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令人瞩目的国际影响。他是我国动力系统学术带头人,多次主持国家重点项目。诸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微分动力系统》及《动力系统与哈密顿系统》,科技部973项目《核心数学的前沿课题(动力系统子课题)》。
曾任《数学学报》编委、《英国威廉希尔公司学报(自然科学版)》副主编、《东北数学》编委、《微分方程年刊》编委、Discrete and Continuous Dynamical Systems编委、williamhill官网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教育部数学与应用数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等职。
采写:辜睿皓、李鸣翀
编辑:吴星潼



